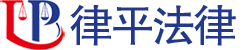确认合同纠纷违约方的赔偿责任应当遵循可预见性原则
发布时间:2019-06-27 浏览次数:442 来自: 律平法律服务成都有限公司
确认合同纠纷违约方的赔偿责任应当遵循可预见性原则
确认合同纠纷违约方的赔偿责任应当遵循可预见性原则——新疆亚坤商贸有限公司与新疆精河县康瑞棉花加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裁判要旨
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确认违约方的赔偿责任应当遵循“可预见性原则”,即违约方仅就其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由于市场风险等因素造成的、双方当事人均不能预见的损失,因非违约方过错所致,与违约行为之间亦没有因果关系,违约方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
1.基本案情
2004 年1 月2 日,亚坤公司与康瑞公司签订棉花购销合同,约定康瑞公司向亚坤公司提供229 级(二级)皮棉1370 吨,单价每吨16 900 元,皮棉质量按国家棉花质量标准GB 1103 - 1999 执行,康瑞公司对质量、重量负责到底,质量、重量出现重大问题,以公证检验为准。后经鉴定显示:康瑞公司向亚坤公司所供皮棉总计:二级皮棉1 . 618 吨;三级皮棉523 . 416 吨;四级皮棉564 . 525 吨;五级皮棉21 . 643 吨,合计重量为1111 . 202 吨,销售货款合计12733 990 . 29 元,亚坤公司货款本金损失为6 659 358 . 11 元。《2004 年棉花市场回顾及2005 年市场展望》一文载明:由于2003 年棉花减产,国内棉花销售价格一度冲至1 . 75 万元/吨的水平。价格如此飙升,既有产需缺口扩大的因素的影响,也有“买涨不买跌”的恐慌心理在起作用。而在国家分两次共增发150 万吨配额和紧缩银根等宏观调控政策引导下,国内棉花价格出现了回落,棉花销售价格在6 月下降到了1 . 5 万元/吨,随后受2004 年棉花大丰收心理预期影响,国内棉花价格跌速加快并冲破了数道心理防线。目前,国内棉花销售价格已经下降到了1 . 13 万元/吨,比年初下降了35%。
1.裁判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棉花购销合同第4 条约定:供方对质量、重量负责到底,质量、重量出现问题,以公证检验为准。故此,康瑞公司对提供给亚坤公司的棉花,在其转让时仍应对质量、重量问题负责到底。在本案双方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康瑞公司向亚坤公司交付的皮棉存在严重的质量和数量问题,导致亚坤公司与新疆博州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加工32支纱、40 支纱的委托加工合同不能履行,亚坤公司买卖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康瑞公司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故亚坤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法院予以支持。
在亚坤公司提取此棉花后,棉花市场价格发生重大变化,棉花价格开始逐月下滑。为防止该批棉花发生因价格下滑造成的损失,截至2005 年2 月7 日,亚坤公司已将康瑞公司交付的棉花全部出售,相互返还已不可能。针对棉花市场价格波动,虽经采取措施补救,但仍造成亚坤公司一 定资金的损失。对亚坤公司因此所蒙受的货款本金损失,康瑞公司理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亚坤公司在棉花价格显著下滑情况下,未及时采取措施,怠于出售,失去棉花销售佳时机,对造成该批棉花本金损失也有一 定过错,亚坤公司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合同签订的2004年1月,恰逢国内棉花市场价格飞涨,但到了2004 年5、6 月以后,棉花市场价格回落,此期间每吨相差5000 ~ 6000 元。亚坤公司在2004 年6 月以后转售的棉花,即使质量等级不变,也必然会出现因市场行情所致的收益损失。原审判决认定的亚坤公司本金损失6 659 358 . 11元不仅包括了棉花减等的差价损失,亦包括在此期间因市场行情下跌所造成的收益损失。该部分收益损失显属市场风险造成的,非为双方当事人所能预见,亦非康瑞公司过错所致。
因康瑞公司与该部分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康瑞公司不应承担市场行情变化导致的亚坤公司的收益损失。原审判决将亚坤公司在市场行情低迷时基于转售关系所形成的销售价格与本案行情高涨时形成的购买价格之差作为亚坤公司的损失由双方分担显属不当,不仅合同关系各不相同,亦有违公平原则及过错责任原则,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亚坤公司关于康瑞公司应补偿其棉花收益损失6 152 857 . 22 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对亚坤公司在购买棉花时所发生的实际损失,即棉花重量亏吨损失及质量减等的差价损失予以确认,对于其他损失部分,即市场风险所致的收益损失、转售期间发生的运输费用、与案外人发生的借贷利息损失,均因缺乏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
代表性学术观点
可得利益赔偿问题的立法表达与司法实践呈现脱节状态,裁判者舍弃立法确立的作为赔偿规则的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转而诉诸立法没有规定的确定性规则。为弥补立法与司法的上述区隔,学理上分别从可预见性规则的完善以及确定性规则的建构两个方面作出如下努力:
吴行政认为(参见:吴行政:《合同法上可得利益赔偿规则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第69~75页),应结合可预见性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司法实践对确定性规则的需求对可预见性规则予以完善并确立确定性规则。就可预见性规则的完善而言,主张:
第 一,区分“通常情形下”的预见与“特别情况下”的预见,对前者借鉴比较法上的立法例引入债权人信息披露义务,作为预见的认定基准。
第二,在适用可预见性规则时应排除故意或重大过失违约。
第三,可预见性规则的内容应明确规定为损害的类型而非程度。
就确定性规则的制度构建而言,主张:非违约方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可得利益的存在及其数额,但人民法院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够推定出可得利益存在的事实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对于可得利益数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裁量。对于可得利益存在的证明标准应根据可得利益本身的未来性、不确定性的特点予以降低,即采取较低盖然性证明标准。对于可得利益的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因果关系和非违约方的过失产生的损失、非违约方没有及时采取合理措施而导致的损失的扩大,以及非违约方因违约而获得的利益的证明,则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刘承韪针对题设问题,提出了违约可得利益损失的确定规则。(参见:刘承韪:《违约可得利益损失的确定规则》,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84~101页。)程序性确定规则的建构以证明标准的降低为价值取向,从三个方面实现:
第 一,引入“合理确定性标准”,即以非违约方所举示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可得利益主张具有“合理确定性”的基础,以此取代可预见规则;
第二,建立“事实与数额区分”的证明标准,即当事人只需要证明损害的“事实”具有合理确定性即可,而无须证明损害的“数额(范围或程度)”具有合理确定性;
第三,放宽自由心证与经验法则的运用,即上述合理确定性标准中的“合理”及事实与数额区分标准中的“数额近似值”需要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和经验法则进行判断,但应以非违约方能够证明有可得利益损失的事实但没有任何可直接参考的标准为适用前提。
实体确定性规则的建构以增强可操作性为价值取向,并以“营业”为中心,对可得利益计算标准进行类型化:
第 一,自身营业利润标准,即以自己的营业利润为标准来计算本次违约给非违约方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
第二,他人营业利润标准,即类推适用和参照执行同行营业利润来计算非违约方的可得利益损失;
第三,新营业标准,即以“新营业规则”来计算新营业可得利益损失;
第四,替代性标准,即上述诸种营业标准难以奏效时,针对违约损害的特殊情境所采取的信赖利益标准、类推适用财产租赁价值或财产信息、机会损失等特殊的替代性标准来支持非违约方的可得利益损失。
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郝丽燕则从多角度论证了“可预见性”要件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并从证明标准角度论证了“确定性规则”的不合理性,取而代之以“极有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即非违约方只要证明可得利益根据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极有可能产生”已足,并就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提出了具体计算或抽象计算方法。(参见:郝丽燕:《违约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确定标准》,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第48~66页。)
此外,学理上对解约与撤销的可得利益赔偿问题也进行了相关探讨。(参见:参见王跃龙:《解约可得利益赔偿之辨》,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5期;尚连杰:《合同撤销与履行利益赔偿》,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5期
案号:高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111 号
案例来源:《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11期
律平法律服务成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8502858003
详细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双楠段90号附5号